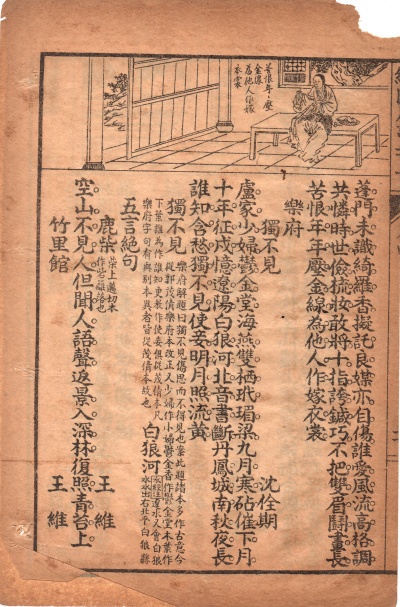独不见
唐·沈佺期
卢家少妇郁金堂,海燕双栖玳瑁梁。
九月寒砧催木叶,十年征戍忆辽阳。
白狼河北音书断,丹凤城南秋夜长。
谁知含愁独不见,更教明月照流黄。
诗题与背景:
这是一首乐府诗。
《古意呈补阙乔知之》是唐代诗人沈佺期创作的一首诗。此诗刻画了一位对远戍丈夫刻骨相思的闺中贵妇形象。诗人通过环境描写烘托思妇的哀怨,以双飞双栖的燕子反衬思妇的孤独,以寒砧催落叶、明月照流黄来烘托离愁别恨。全诗情思缱绻,辞藻典雅,韵味悠深,意境鲜明,被历代诗评家认为是温丽高古之佳篇。
独不见,乐府杂曲歌名,内容写不相见之苦。题一作《古意呈乔补阙知之》。
补阙:官名。武则天时始置,有左右之分。乔知之:唐代同州冯翊(今陕西大荔)人,以文词知名。
此诗名为乐府,实是七律(故未入卷四七言乐府);题一作“古意”,实咏今事。先以开头两句写一对年轻夫妇,同处在繁华的长安城,就像海燕之双棲于高堂的画梁,以后便是一别十载,少妇也感流光已逝。五六两句,分写行者居者。“收拓开一步,正是跌进一步。曲折圆转,如弹丸脱手。”
独不见:乐府《杂曲歌辞》旧题。《乐府解题》:“独不见,伤思而不见也。”
独不见:乐府《杂曲歌辞》旧题。《乐府解题》:“独不见,伤思而不见也。”题一作《古意呈乔补阙知之》,疑为副题。乔补阙为乔知之,武则天万岁通年间任右补阙,诗当作于此时。
此诗在宋人郭茂倩的《乐府诗集》卷七五中题为“独不见”,而最早收录此诗的敦煌残卷《珠英学士集》题作“古意”,在北宋初期编成的《文苑英华》卷二〇五中也题作“古意”,在五代韦縠所编的《才调集》卷三中,题为“古意呈乔补阙知之”,在《全唐诗》卷九六中题为“古意呈补阙乔知之”。据题意可知此诗是写给时任补阙的乔知之的。
清人毛奇龄《西河诗话》云:“沈詹事 《古意》,《文苑英华》与本集题下皆有‘赠补阙乔知之’六字,因詹事仕则天朝,适乔知之作补阙,其妾为武承嗣夺去,补阙剧思之,故作此,以慰其决绝之意。言比之征夫戍妇,无如何也。故结云‘谁谓’,言不料其至此也。后补阙竞以此事致死,此行文一大关系者。自选本删题下六字,遂昧此意久矣。”莫砺锋则认为此说没有充足的理由。乔知之在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中均有传,在武后时任左补阙。垂拱二年(686)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出师北征同罗、仆固,乔知之受敕摄侍御史护其军,这在陈子昂的《燕然军人画像铭》中有明确记载。沈佺期此诗当即作于此时,故称乔为“补阙”。待到此役毕后,乔知之回朝并迁左司郎中,其妾被夺事发生于载初元年(690),也即天授元年(是年九月改元天授),这在《本事诗》中有明确记载,《本事诗》中称乔知之为“左司郎中”,也很准确。乔知之被杀一事,《唐历》和《新唐书·则天皇后纪》都系于天授元年。因此,当沈佺期作此诗时,乔知之妾被夺之事尚未发生。莫砺锋推测沈佺期作此诗赠予乔知之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乔知之作诗爱写有关怨妇或男女相思的题材,二是乔知之曾有随军北征的经历,沈诗既写征人、思妇之事,便将它题赠给即将出征的乔知之,或者沈诗就是为送乔出征而作。
逐句释义:
卢家少妇郁金堂,海燕双栖玳瑁梁:
郁金香涂饰在卢家少妇的楼堂,海燕栖息在用玳瑁装饰的屋梁。
卢家年轻的主妇,居住在以郁金香浸洒和泥涂壁的华美的屋宇之内,海燕飞来,成对成双地栖息于华丽的屋梁之上。
卢家少妇:梁武帝萧衍诗中的人物,后来泛指少妇。萧衍《河中之水歌》有诗句:“十五嫁为卢家妇,十六生儿字阿侯。卢家兰室桂为梁,中有郁金苏合香。”
郁金堂:以郁金香料涂抹的堂屋。郁金,郁金香,百合科植物,可浸酒涂壁。堂,一作“香”。
海燕:即越燕,多在梁上作巢。
玳瑁(旧读mèi)梁:指画梁。玳瑁,龟属海产动物,可作装饰品。
九月寒砧催木叶,十年征戍忆辽阳:
在九月的捣衣声中树叶已落尽,思念着在辽阳征戍十年的丈夫。
九月里,寒风过后,在急切的捣衣声中,树叶纷纷下落,丈夫远征辽阳已逾十载,令人思念。
砧(zhēn):捣衣石。古代捣衣多在秋晚。
催木叶:指砧声至秋而起,树叶也随秋而落。
戍:驻守。
辽阳:指今辽宁辽阳市附近地区,为东北边防要地。
白狼河北音书断,丹凤城南秋夜长:
丈夫在渺茫的白浪河音讯不通,京城中的我总觉日夜过得漫长。
白狼河北的辽阳地区音信全部被阻断,幽居在长安城南的少妇感到秋日里的夜晚特别漫长。
白狼河:白狼水,即今辽宁境内的大凌河。
丹凤城:此指长安。一说因秦穆公女吹箫,凤降其城,故名。后便为京城之别称。按,恐即凤阙之意。汉建章宫有凤阙,后世也借指帝城,唐代民居多在城南。
谁知含愁独不见,更教明月照流黄:
谁能够看见她的孤独她的悲愁,只把那明月清辉洒落在纱帐上。
她哀叹:我到底是为哪一位思而不得见的人满含哀愁啊?为何还让那明亮的月光照在帏帐之上?
谁知:一作“谁为”;一作“谁谓”。
更教:一作“使妾”。
流黄:黄色的绢,这里泛指少妇所用的丝织品,如巾或帷。一说指衣裳。
作品赏析:
这是一首思妇诗。诗题《独不见》系沿用乐府“杂曲歌辞”旧题,原意是“伤思而不得见也”。一作《古意呈乔补阙知之》。虽借用乐府题目,但采用当代题材,其实是一首完整的七律诗。它写一位长安少妇对征戍辽阳十年未归的丈夫的殷切思念。笔调缠绵悱恻,委婉流畅,反映出诗人对这些妇女同情之心。
此诗名为乐府,实是七律(故未入卷四七言乐府);题一作“古意”,实咏今事。先以开头两句写一对年轻夫妇,同处在繁华的长安城,就像海燕之双棲于高堂的画梁,以后便是一别十载,少妇也感流光已逝。五六两句,分写行者居者。“收拓开一步,正是跌进一步。曲折圆转,如弹丸脱手。”(《昭昧詹言》)
《独不见》写的是一个长安少妇因丈夫久戍辽阳,十年不归,造成她独守空闺的孤寂和相思的痛苦。
这首七律,是借用了乐府古题“独不见”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解题云:“独不见,伤思而不得见也。”本诗的主人公是一位长安少妇,她所“思而不得见”的是征戍辽阳十年不归的丈夫。诗人以委婉缠绵的笔调,描述女主人公在寒砧处处、落叶萧萧的秋夜,身居华屋之中,心驰万里之外,辗转反侧,久不能寐的孤独愁苦情状。
这首七律,是借用了乐府古题“独不见”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解题云:“独不见,伤思而不得见也。”此诗的主人公是一位长安少妇,她所“思而不得见”的是征戍辽阳十年不归的丈夫。诗人以委婉缠绵的笔调,描述女主人公在寒砧处处、落叶萧萧的秋夜,身居华屋之中,心驰万里之外,辗转反侧,久不能寐的孤独愁苦情状。此诗对后来唐代律诗,尤其是边塞诗影响很大,历来评价甚高。姚鼐说它“高振唐音,远包古韵,此是神到之作,当取冠一朝矣。”
此诗的主人公是一位长安少妇,她所“思而不得见”的是征戍辽阳十年不归的丈夫。诗人以委婉缠绵的笔调,描述女主人公在寒砧处处、落叶萧萧的秋夜,身居华屋之中,心驰万里之外,辗转反侧,久不能寐的孤独愁苦情状。此诗对后来唐代律诗,尤其是边塞诗影响很大,历来评价甚高。姚鼐说它“高振唐音,远包古韵,此是神到之作,当取冠一朝矣。”
首联“卢家少妇郁金堂,海燕双栖玳瑁梁”
“卢家少妇郁金堂,海燕双栖玳瑁梁。”卢家少妇,名莫愁,梁武帝萧衍诗中的人物,后来用作少妇的代称。郁金是一种香料,和泥涂壁能使室内芳香;玳瑁是一种海龟,龟甲极美观,可作装饰品。开头两句以重彩浓笔夸张地描绘女主人公闺房之美:四壁以郁金香和泥涂饰,顶梁也用玳瑁壳装点起来,多么芬芳,多么华丽啊!连海燕也飞到梁上来安栖了。“双栖”两字,暗用比兴。看到梁上海燕那相依相偎的柔情密意,这位“莫愁”女也许有所感触吧?
诗开篇就突出了女主人公的姓氏和身份:“卢家少妇郁金堂,海燕双栖玳瑁梁。”首联两句以重彩浓笔夸张地描绘女主人公闺房之美:四壁以郁金香和泥涂饰,顶梁也用玳瑁壳装点起来,无比芬芳,无比华丽。连海燕也飞到梁上来安栖了。“双栖”两字,暗用比兴。看到梁上海燕那相依相偎的柔情密意,这位“莫愁”女也许有所感触吧。此诗开头用浓墨重彩描写少妇居室之华丽,正是为反衬其心情之孤寂哀伤,这与用“海燕双栖”来反衬人单影只是同样的道理。
首联言夫妇应如雕梁上的燕子,双宿双飞。“卢家少妇”典出萧衍的《河中之水歌》: “河中之水向东流,洛阳女儿名莫愁。莫愁十三能织绮,十四采桑东陌头,十五嫁为卢家妇,十六生儿字阿侯。卢家兰室桂为梁,中有郁金苏合香。”卢家少妇的活动环境极为华美:郁金香和泥涂抹于闺房四壁,香气袭人,来自南海的燕子成双停栖于玳瑁装饰的画栋之上。可是,在这华丽典雅的房中,女主人公却只能独守其间,与“海燕双栖”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以双燕起兴,引起下文表述少妇独守之苦。
诗开篇即突出女主人公的姓氏和身份——卢家少妇。卢家少妇出自萧衍《河中之水歌》:“河中之水向东流,洛阳女儿名莫愁。莫愁十三能织绮,十四采桑东陌头,十五嫁为卢家妇,十六生儿字阿侯。卢家兰室桂为梁,中有郁金苏合香。”“郁金堂”、“玳瑁梁”,用来形容卢家少妇居室的华丽精美,是从富贵方面写少妇的身份与地位。海燕双栖在玳瑁梁上,相偎相依,相亲相爱,衬托出思妇的形单影只、孤寂难耐,这是暗写。诗人特别点明她是一位“少妇”,正当青春妙龄、渴求爱情之时,这种愁苦之情就更不堪忍受了。首二句通过女主人公居室环境的描写用人与燕对比,从侧面写思妇的孤独。乍看起来,诗人是作客观叙述,实则充满了对思妇的同情。
颔联“九月寒砧催木叶,十年征戍忆辽阳” 此时,又听到窗外西风吹落叶的声音和频频传来的捣衣的砧杵之声。秋深了,天凉了,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御冬的寒衣,有征夫游子在外的人家,就更要格外加紧啊!这进一步勾起少妇心中之愁。“寒砧催木叶”,造句十分奇警。分明是萧萧落叶催人捣衣而砧声不止,诗人却故意主宾倒置,以渲染砧声所引起的心理反响。事实上,正是寒砧声落叶声汇集起来在催动着闺中少妇的相思,促使她更觉内心的空虚寂寞,更觉不见所思的愁苦。夫婿远戍辽阳,一去就是十年,她的苦苦相忆,也已整整十年了!
从首联到颔联,场景从室内移向室外之寒砧木叶,情思则从眼前移向远方。此时,少妇听到窗外西风吹落叶的声音和频频传来的捣衣的砧杵之声。秋深了,天凉了,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御冬的寒衣,有征夫游子在外的人家,就更要格外加紧了。这进一步勾起少妇心中之愁。“寒砧催木叶”,造句十分奇警。分明是萧萧落叶催人捣衣而砧声不止,诗人却故意主宾倒置,以渲染砧声所引起的心理反响。事实上,正是寒砧声落叶声汇集起来在催动着闺中少妇的相思,促使她更觉内心的空虚寂寞,更觉不见所思的愁苦。夫婿远戍辽阳,一去就是十年,她的苦苦相忆,也已整整十年了。
颔联说到丈夫久别远征。时已九月秋深,在急切的捣衣声中,枯叶纷纷落下,人们正赶制寒衣。古人制寒衣,先把绢素一类衣料放在砧上捣软,再裁制成衣。这位少妇听到捣衣声,不免想起戍守辽阳的丈夫,屈指一算别后竟已十年了,她的心禁不住飞到前线。由寒砧而引起对丈夫的思念,这表现了女性特有的性格。
卢家少妇因孤寂而思夫致使深夜不眠,窗外传来阵阵捣衣声,更撩起她的思念之情:“九月寒砧催木叶,十年征戍忆辽阳。”“九月”,正是深秋时候,家家户户为征人准备寒衣,秋天夜晚是一片捣衣声。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,李白所描绘的正是此情此景。这萧萧落叶、笃笃砧声,就像飘落在床前、敲打在心上,使思妇心碎。“九月寒砧”句,构思奇特,好像是九月的砧声把秋叶纷纷催下,这是一种错觉,其实是落叶催促人们捣衣。句式之所以倒装,是突出砧声之响、之急,同时也是为了格律诗平仄的需要。这种倒置句式,在古典诗词中常见,如清代徐灿《如梦令》:“生怕子规声,啼绿庭前芳草。”暮春时,草已绿,正是子规啼鸣之时,而诗人却要说成怕子规声把草催绿了,所用的表现手法与“九月”句相同。秋叶飘落,一派萧索景象,渲染了凄凉气氛,是从侧面继续写少妇的痛苦心情。因为“寒砧”使人不能入睡,自然联想到远在异地的征夫:“十年征戍忆辽阳。”“辽阳”,在今辽宁省境内,为当时东北边防要地,便是少妇的丈夫戍守的地方。“十年征戍”,丈夫在边塞戍守已经十年了,边塞苦寒,沙场征战,受尽了种种磨难;而自己独守空闺,苦苦相思,盼望了一年又一年,每当秋来砧急,思情尤甚,诗人用一个“忆”字,把遥隔万里的思妇征夫联系起来,把妻子对丈夫的深情突现出来。其中,还暗寓了她对战争的怨恨,对和平的期望。
颈联“白狼河北音书断,丹凤城南秋夜长”出句的“白狼河北”正应上联的辽阳。十年了,夫婿音讯断绝,他现在处境怎样?命运是吉是凶?几时才能归来?还有无归来之日?……一切一切,都在茫茫未卜之中,叫人连怀念都没有一个准着落。因此,这位长安城南的思妇,在这秋夜空闺之中,心境就不单是孤独、寂寥,也不只是思念、盼望,而且在担心,在忧虑,在惴惴不安,愈思愈愁,愈想愈怕,以至于不敢想象了。上联的“忆”字,在这里有了更深一层的表现。
颈联单承第四句,写远征之戍人与居家之思妇。“白狼河北”正应上联的“辽阳”,从对方落笔。女主人公在想音讯断绝十年的夫婿的处境、命运、归期等。这一切一切,都在茫茫未卜之中,叫人连怀念都没有一个准着落。因此,这位长安城南的思妇,在这秋夜空闺之中,心境就不单是孤独、寂寥,也不只是思念、盼望,而且在担心,在忧虑,在惴惴不安,愈思愈愁,愈想愈怕,以至于不敢想象了。上联的“忆”字,在这里有了更深一层的表现。
颈联是颔联意境的深化。“白狼河”,在辽阳; “丹凤城”,指长安。“白狼河北音书断”,紧顶“十年”,分别十年,鸿雁失落,音讯杳无,前方征人吉凶未卜。下句紧顶“九月”,长安城南少妇独守空闺,秋夜漫漫,能不愁思绵绵?这里“忆”的内容进一步的具象化了。
颈联紧承颔联,进一步写相思之苦。“白狼河”,古称白狼水,即今辽宁省的大凌河,是征夫戍边的所在地。“音书断”,因丈夫没有书信捎回,压根儿不知其是吉、是凶、是死、是活,所以引起妻子日夜不安的悬念,这句是从对方落笔;而“丹凤城南”句则是转为写自己的痛苦。“丹凤城”,即长安城,唐时长安城的宫阙中有丹凤门,所以称为“丹凤城”,是女主人公居住的地方,也是相思的所在。夜晚,辗转不寐,埋怨秋夜太长,这对一个思妇来说是够痛苦的了,何况是萧瑟凄凉的秋夜,使她受相思和哀怨煎煮,更是难耐难熬。上句重在写“音书断”,下句突出“秋夜长”,都是渲染思妇的愁苦心态。此联行文回环,交错互补,意味幽深。以上两联,对仗十分工整,不仅词性和意义相对,而且也讲究声律,由此可见诗人“研练精切”,所以被元稹誉之为“律诗”,成为律诗形成的标志。
尾联“谁知含愁独不见,更教明月照流黄”
寒砧声声,秋叶萧萧,叫卢家少妇如何入眠呢!更有那一轮恼人的明月,竟也来凑趣,透过窗纱把流黄帏帐照得明晃晃的炫人眼目,给人愁上添愁。前六句是诗人充满同情的描述,到这结尾两句则转为女主人公愁苦已极的独白,她不胜其愁而迁怒于明月了。诗句构思新巧,比之前人写望月怀远的意境大大开拓一步,从而增强了抒情色彩。
尾联写少妇之愁无人得知,只有月光映照织机。寒砧声声,秋叶萧萧,叫卢家少妇无法入眠;更有那一轮恼人的明月,竟也来凑趣,透过窗纱把流黄帏帐照得明晃晃的炫人眼目,给人愁上添愁。前六句是诗人充满同情的描述,到这结尾两句则转为女主人公愁苦已极的独白,她不胜其愁而迁怒于明月。诗句构思新巧,比之前人写望月怀远的意境大大开拓一步,从而增强了抒情色彩。
尾联点明题意,明说“愁”字。其实岂只是愁,还有怨。“流黄”,指帷帐。两句极写少妇的失意与惆怅。
结尾二句抒发感慨,收束全篇:“谁为含愁独不见,更教明月照流黄。”“流黄”,是黄紫间色的绢。这是什么?有三说: 一说是所捣之衣,一说是机中织残的绢匹,一说是帐幔。前二说与少妇所处的地位“郁金堂”、“玳瑁梁”等欠合,所以后说较为合理。这二句的意思是:我本因相思不得成眠,而明月还故意捉弄我,偏偏照在帐幔之上,清彻如昼,把睡意全搅去了。女主人公将相思的痛苦及对战争的怨恨一股脑儿发泄给明月,实属无奈,似为无理,但更显情深。 全诗情思缱绻,哀怨低徊,韵味悠深,催人泪下。
这首诗,人物心情与环境气氛密切结合。“海燕双栖玳瑁梁”烘托“卢家少妇郁金堂”的孤独寂寞,寒砧木叶、城南秋夜,烘托“十年征戍忆辽阳”、“白狼河北音书断”的思念忧愁,尾联“含愁独不见”的情语借助“明月照流黄”的景物渲染,便显得余韵无穷。论手法,则有反面的映照(“海燕双栖”),有正面的衬托(“木叶”、“秋夜长”),多方面多角度地抒写了女主人公“思而不得见”的愁肠。诗虽取材于闺阁生活,语言也未脱尽齐梁以来的浮艳习气,却显得境界广远,气势飞动,读起来给人一种“顺流直下”(《诗薮·内编》卷五)之感。
卢家句,梁武帝萧衍《河中之水歌》:“河中之水向东流,洛阳女儿名莫愁。十五嫁为卢家妇,十六生儿字阿侯。卢家兰室桂为梁,中有郁金苏合香。”此句用其意。郁金,郁金香,可浸酒涂壁,百合科,旧谓出大秦国,即今小亚细亚。
海燕,即越燕,多在梁上作巢。玳瑁(旧读妹mèi)梁,指画梁。玳瑁,龟属海产动物,可作装饰品。这句是以双燕起兴,先比夫妇相守,后托少妇独处。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:“双燕双飞绕画梁,罗帏翠被郁金香。”
谁为两句,原是用现成的题意,意谓谁使她含愁而不能相见(有双关意),却还要教明月来照流黄。谁为,也可解作“为谁”。流黄,黄色的绢,这里泛指少妇所用的丝织品,如巾或帷。更教,一作“使妾”。
这首诗,人物心情与环境气氛密切结合。“海燕双栖玳瑁梁”烘托“卢家少妇郁金堂”的孤独寂寞,寒砧木叶、城南秋夜,烘托“十年征戍忆辽阳”“白狼河北音书断”的思念忧愁,尾联“含愁独不见”的情语借助“明月照流黄”的景物渲染,便显得余韵无穷。论手法,则有反面的映照(“海燕双栖”),有正面的衬托(“木叶”、“秋夜长”),多方面多角度地抒写了女主人公“思而不得见”的愁肠。诗虽取材于闺阁生活,语言也未脱尽齐梁以来的浮艳习气,却显得境界广远,气势飞动,读起来给人一种“顺流直下”(《诗薮·内编》卷五)之感。
从体裁来看,此诗既是一首乐府诗,又是一首七言律诗,《唐诗三百首》就将它归入“七律·乐府”类。既是七律,后人便从七律发展史的角度对它有所评论。鉴于这首诗情思缱绻,哀怨低徊,韵味悠深,影响较大,有人对它非常推崇,明人何景明、薛蕙甚至誉之为“唐人七律第一”。
这首诗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演变,轨迹分明,由盼望到回忆,到音书断,到愁、怨,步步递进上升。最后写明月照床前,以景语刹尾,以不了了之,其实余音未断,不仅表明少妇愁思之长,也发人深思。
这首诗在构思上十分讲究意境的时空交叉安排。在时间上,短时态有: “海燕双栖”的春天,“秋夜长”的九月;长时态有: “十年”。空间上,以郁金堂为中心,近者延及玳瑁梁、木叶、丹凤城,远者波及辽阳、白狼河。通过对这些诗的意象的选取,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妇怀征人图,大大加浓了抒情意味。因此,说这首诗是初唐较早出现的优秀七律之一,决非过誉。
名家点评:
明·郭濬《增订评注唐诗正声》:此诗比兴多,用古绝不堆垛。
明·杨慎《升庵诗话》卷十:宋严沧浪取崔颢《黄鹤楼》诗为唐人七言律第一,近日何仲默、薛君采取沈佺期“卢家少妇郁金堂”一首为第一,二诗未易优劣。或以问予,予曰:崔诗赋体多,沈诗比兴多。
明·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:何仲默取沈云卿《独不见》,严沧浪取崔司勋《黄鹤楼》,为七言律压卷。一诗固甚胜,百尺无枝,亭亭独上,在厥体中,要不得为第一也。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,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。如织宫锦间一尺绣,锦则锦矣,如全幅何?
明·郝敬《批选唐诗》:化近体为古意,风韵淹雅,而略少意趣。近体不主意而主风韵,故冠冕初唐不可易也。
明·胡应麟《诗薮·内编》卷五:卢家少妇,体格丰神,良称独步,惜颔颇偏枯,结非本色。同乐府语也,同一人诗也。然起句千古骊珠,结语几成蛇足。
明·陆时雍《唐诗镜》:高古浑厚,绝不似唐人所为。三、四迥出常度,结更雄厚深沉。
明·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:沈诗篇题原名《独不见》,一结翻题取巧,六朝乐府变声,非律诗正格也。
明·周珽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》:钱光绣云:语语从古调淘洗,作律诗看佳,作乐府看亦佳。周珽曰:深情老笔,此十年梨花枪也。陈继儒曰:云卿初变律体,如此篇虽未离乐府馀调,而落笔圆转灵通,要是腹角出龟龙、牙缝具出赤绿者。
明·邢昉《唐风定》:“起语千古骊珠,结句几成蛇足”,此论吾不谓然。六朝乐府,行以唐律,瑰玮精工,无可指摘。
清·王夫之《唐诗评选》:从起入颔,羚羊挂角;从颔入腹,独茧抽丝。第七句蛳吼雪山,龙含秋水。合成旖旎,韶采惊人。古今推为绝唱,当不诬。其所以如大辨才人说古今事理,未有豫立之机,而鸿纤一致,人但歆歆于其珠玉。
清·朱之荆《增订唐诗摘钞》:燕双栖而人独宿,此反映法。愁不见月,倍增愁思,故怨及无情,若有人指使而然。
清·吴乔《围炉诗话》:八句如钩锁连环,不用起承转合一定之法者也。
清·毛张健《唐体馀编》:仍本六朝艳体,而托兴深婉,得风人之旨,故为佳什。若王、李诸公必以此为七律第一首,则吾又不得其解也。
清·谭宗《近体秋阳》:纯乎古作,安得不高?《凤凰台》、《黄鹤楼》,要彼命篇实有不同尔,即以体气论,吾未见能过此也。
清·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卷上:云卿《独不见》一章,骨高,气高,色泽情韵俱高,视中唐“莺啼燕语报新年”诗,味薄语纤,床分上下。
清·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:本以燕之双栖兴少妇独居,却以“郁金堂”、“玳瑁梁”等字攒成异彩,五色并驰,令人目眩,此得齐梁之秘而加神妙者。三四不过叙流年时景,而措语沉着重稳。五六句分写行者,居者,匀配完足,复以“白狼”、“丹凤”攒染设色。收拓并一步,正跌进一步。曲折圆转,如弹丸脱手,远包齐梁,高振唐音。
清·张世炜《唐七律隽》:崔赋体多,沈比兴多,以画家法论之,沈诗披麻皴,崔诗大斧劈皴也。余意诗无定品,兴会所至,自能动人,然须才法两尽。崔诗才气胜,沈诗法律胜,以三唐人诗而必以孰为第一,何异旗亭甲乙耶?
作者简介:
沈佺期(约656—714年),唐朝诗人。字云卿,相州内黄(今属河南)人。上元进士,官至中书舍人、太子少詹事。曾因贪污及谄附张易之,被流放驩州。诗与宋之问齐名,多应制之作。流放时期的作品,则多对其境遇表示不满。律体谨严精密,对律诗体制的定型颇有影响。原有集,已散失,明人辑有《沈佺期集》。《全唐诗》编其诗三卷,收录其诗作171首。(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、《唐才子传》卷一)